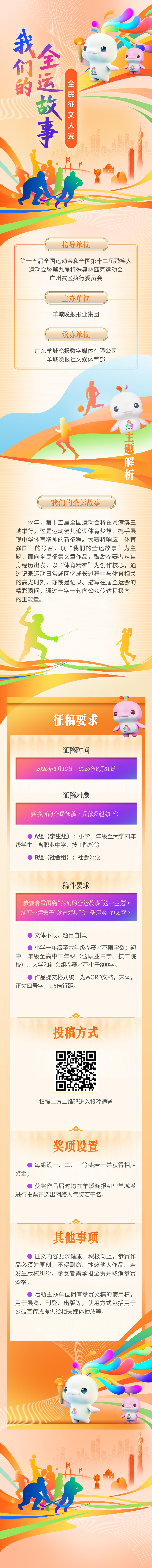发令枪响时,刘泽蛟听见铁链坠入水中的脆响——这是铁人三项游泳赛段引导绳的信号。当他跃入泳池,双臂划水声里藏着28枚奖牌的记忆;但此刻,他要征服的不仅是750米的公开水域,还有接踵而至的20公里自行车与5公里长跑。
截至目前参与的30余场赛事,取得28枚奖牌背后,是清晨泳池里的孤独划水,是手掌磨出的厚茧,更是把“不可能”嚼碎咽下的倔强。在2009年破格成为特校教师后,他本可安享荣誉,却因全国残特奥会新立项的铁人三项再次出征,对他来说游泳是舒适区,铁三则是要征服的三座大山。他说:“别人用眼睛看赛道,我用汗水尝它的味道。”当特奥会圣火燃起时,这位看不见光的运动员,终将让世界看见,真正的光明,永远生长在心里。

泳池里的“光”,从摸索到绽放
1989年的春天,刘泽蛟出生在武冈市晏田乡的农家。母亲孕期误服的药物,让他的世界永远停留在“光感”的边缘。2001年,12岁的他被父亲送进武冈市特殊学校,第一次摸到盲文课本时,指尖的凹凸让他觉得“像在水里抓不住的鱼”。直到两年后,长沙特殊学校进行选拔运动员,原本是参加田径的,但奈何身高等原因被婉拒门外。好在敢于尝试的他,得到游泳教练的青睐,教练拍着他的肩膀说“这孩子臂展好,是块料子”,他的人生才照进另一束光。
最初在泳池里,他总撞向池壁,额头青一块紫一块。教练教他数划水次数:“10米需要6次划臂,转身前还有3次机会调整。”他就抱着浮板,在水里一遍遍数,直到耳朵能分辨水流声的细微变化——左边水声变急,是快到边界了;右边传来队友的呼吸,要及时避让。2007年世界残疾人游泳公开赛100米仰泳决赛,他游到最后20米时,突然听不到熟悉的节奏声,瞬间慌了神。但肌肉记忆救了他,凭着“最后12次划臂必须触壁”的本能,他率先撞线,用自己的拼搏与汗水,第一次站在了世界的领奖台上,拿到人生第一枚国际金牌。站在领奖台上,听着国歌响起,他悄悄数着掌声的次数,心里比谁都清楚:“这枚金牌,是用几千次‘数错了重来’换的。”
铁三赛道的“难”,把每一步都变成“路标”
“游泳是水托着我,铁三是我拖着自己往前闯。”刘泽蛟这样形容转型的挑战。已经36岁的他,在2024年决定尝试铁人三项时,身边人都劝他:“你都拿14块金牌了,见好就收吧。”他却笑:“水里的路走熟了,想试试路上的。”可这条路远比想象中难。游泳之后的骑行环节,他得和引导员并排骑行,靠耳机里的指令判断转弯、加速。第一次训练,他跟着“左拐”的指令倾斜车身,却因为没把握好角度,连人带车摔进草丛,手肘擦出长长的血痕。“不疼,就是觉得对不起车。”他爬起来,让引导员把路线分解成“50米后有个小坡”“转弯前会敲三下车架”,记在小本子上,睡前摸黑再“走”一遍。
跑步更是对“光感”的极致考验。跑道的触感、地砖接缝的震动、路面坡度的细微变化,都成了他的“眼睛”。有次在操场训练,突然下起小雨,路面变滑,他一脚踩空,膝盖磕在台阶上。缓过来后,他反而笑了:“这下记住了,下雨天脚步声会变闷,得提前减速。”如今训练场上,他的自行车把立绑着震动传感器,转弯时通过触觉辨向;跑步时,与引导员拉着弹力绳,每一次拉扯都是前进指令。这些特制器械成了他的“视网膜”,而摔破的膝盖、磨烂的手套,则记录着突破极限的代价。因为他能从泳池里站起来,就能在跑道上走下去”
讲台前的“暖”,把自己活成“参照物”
在武冈市特殊学校的泳池边,总能看到刘泽蛟手把手教孩子划水。“小臂再弯一点,水的阻力才大。”他握着盲童的手,让他们感受水流从指缝溜走的触感。2009年他被破格录用为教师时,校长说:“你不用讲太多大道理,站在那里就是最好的课。”学生肖唐浩曾因先天残疾自暴自弃,刘泽蛟带他去看自己的奖牌:“这块银牌,是我2021年残运会拿的,当时我32岁,比你现在还大。”他给肖唐浩讲自己摔在铁三赛道上的事,“疼是真的,但爬起来的劲儿,比疼更厉害。”后来,肖唐浩在全国残运会上拿到金牌,回来第一时间抱住他:“刘老师,我终于知道你说的‘劲儿’是什么了!”在他培养的学生里,1人获得世界残奥会银牌、4人获得全国残运会金牌。学生眼中的他是追逐光明的引路人。
如今每天清晨,草叶凝着微凉的露水,刘泽蛟已早早到了训练场,闭着眼走圈,数着步数,像在丈量自己的人生。“我看不见路,但每一步踩实了,路就出来了。”他说这话时,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脸上,那双模糊的眼睛里,仿佛有光在流动——那是比阳光更亮的,属于坚韧者的光。无论铁三比赛成绩如何,刘泽蛟的参与本身就是对“不可能”的反驳。他或许看不清世界的色彩,但他的故事,让更多人看见了“坚韧”该有的样子。未来,他还将继续挑战,那束“光感”也会在新的征程中延续,激励更多人勇敢逐梦 。
文|冉红梅 广东金融学院 记者柴智整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