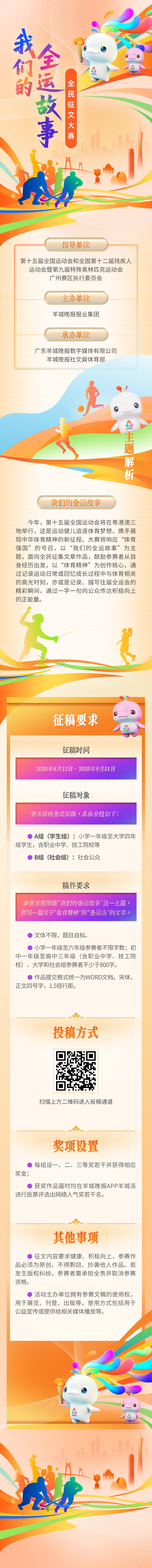晨光初破,珠江水面浮动着粲然金斑。海心沙广场上,几簇工人正调试着巨大的电子火炬装置,金属支架在晨晖中如铮铮铁骨,静候着11月那场席卷粤港澳的圣火。我驻足凝望这座即将沸腾的城池,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苍劲的慨叹:“第一届全运会的跑道,还是煤渣铺的呐。”回身望去,一位白发老者拄杖立于江风之中,深陷的眼窝里藏着两个燃烧的火种——那是一个民族在体育长路上跋涉66年后,沉淀在个体生命中的精神星光。

1959年的秋光里,首届全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揭幕。煤渣跑道在运动员脚下扬起烟尘,如简陋舞台上腾起的金色帷幕。那会徽上金麦穗环抱的“1”字,恰似冲出起跑线的箭头。彼时百废待兴的国度,将赛场当作向世界证明生命韧性的战场。有位短跑选手在百米决赛前夜,悄悄用砂纸磨平了起跑钉鞋的豁口。发令枪响时,他足下的铁钉深深扎进煤渣里,每一步都踏出星火。冲过终点时血染跑鞋,却浑然不觉痛楚。当广播宣布新纪录诞生,他忽然蹲下身去,用颤抖的手指抚摸跑道——那黝黑的煤渣里,埋着整个民族对尊严的渴求。66年光阴流转,当年磨平钉鞋的少年已成耄耋,可每当电视里响起全运赛场的呐喊,他干枯的掌心仍会沁出汗水,仿佛又摸到煤渣粗粝的质感。体育精神在血脉里生根,远比奖牌更恒久。
全运赛场从不缺少青春的身影。在游泳馆的蔚蓝水域中,16岁的广东女孩曾用身体丈量着梦想的刻度。蝶泳决赛前夜,教练在她掌心写下“破茧”二字。发令笛响时,她如刀锋劈开水面,每一次换气都吞咽着含氯的水汽。最后50米,乳酸在肌肉里炸开烈焰,看台上母亲的呼唤穿透水波:“阿女,你系浪啊!”她猛然惊醒般提速,触壁时电子屏迸出金芒——比第二名快出0.01秒。多年后她成为泳池边的教练,当小队员因0.1秒之差落泪时,她翻开珍藏的奖牌,“你看,当年我赢0.01秒,如今你输0.1秒,这微小的差距里,藏着下次腾跃的空间。”胜负不过是刻度尺上的标记,真正不朽的,是那永不停歇的自我超越。
而赛场之外,体育精神在无数普通人身上绽放微光。志愿者小林的故事让我动容,四年前在西安奥体中心,她负责接待视障田径选手。当引导员牵引着盲人跑者踏上四百米跑道时,小林忽然听见身旁传来压抑的抽泣。一位中年志愿者望着运动员腕间的牵引绳,泪水浸湿了口罩,“我女儿也是视障...…原来她们能在风里飞起来。”次日小林申请调入陪跑组,当她手腕与盲人运动员系上同一根红绳,发令枪响的刹那,两个人的心跳在共振中合成同一个节拍。冲线时她们摔作一团,却爆发出酣畅的笑声。那根红绳后来被收进全运纪念馆,标签上写着:“联结人心的纽带,比终点线更长”。
此刻站在珠江畔,我看见晨练的老人在“全民全运”的巨幅海报前打太极,白衣飘飘如展翅银鸥;少年踩着滑板掠过滨江绿道,身影在朝阳里拉成金色的直线。体育精神早已溢出赛场边界,化作城市肌理中的活力因子。全运会徽上燃烧的火炬,此刻正映照在志愿者胸前的徽章里,闪烁在少年追逐的篮球上,荡漾在老人舒展的眉宇间。
圣火即将在粤港澳三地同时点燃。当焰火照亮珠江、香江、濠江的水波,我们将看见体育精神最本真的模样——它不仅是奖台上的荣耀时刻,更是一个民族在奔跑中不断确认自身重量的过程。那些汗水浸透的坚持,那些伤痛淬炼的意志,那些交融在接力棒上的温度,终将汇聚成塑造国民品格的磅礴力量。跑道延伸处,是无数个体生命在突破自我疆界时爆发的光热,这些光热交织成网,托举起一个民族向心力的道场。
夜幕降临时,珠江两岸华灯初上。电子火炬装置开始试运行,赤红的火焰光影在楼宇间流转,如不息的血脉奔涌。我忽然读懂那老者眼中的星光——当六十六载光阴在圣火中流转激荡,跑道早已化作文明的轨迹,赛场已然成为生命的道场。在这里,每个普通人都是主角,每次跳跃都是对生命极限的叩问,每滴汗水都在浇灌着名为“中华精神”的参天巨树。
文|温戴伦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记者 柴智整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