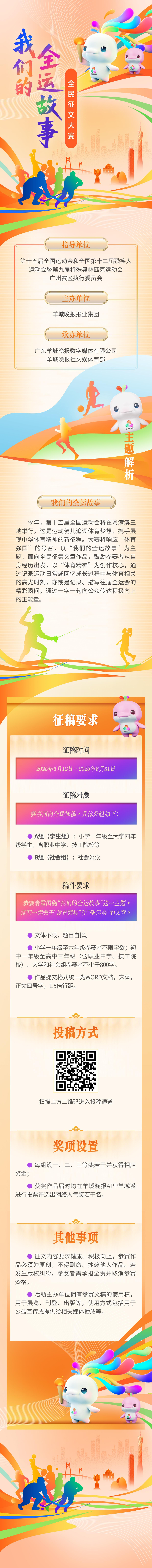沙水的汽濡湿了初夏的晚风,我倚在栏杆上,望见对岸高楼上的灯光次第亮起,像无数双眼睛温柔地注视着这条奔流不息的河流。再过些日子,这里将点燃残特奥会的圣火,而紧随其后的,是全国第十二届残运会的旗帜飘扬。我心中所涌动的不止是对赛事本身的期待,更是对那些即将在这片热土上书写生命韧性与力量的人们,一种近乎虔诚的期待。

那日黄昏,我遇见一个叫小舟的姑娘在河边步道上摸索前行,她的手指轻轻搭在导盲犬安森的背脊上。安森是一条沉稳的金毛,步伐稳健,如同最忠实的影子。“我们在练习,”她笑着告诉我,声音里没有迟疑的阴翳,“为了参加盲人门球。”她的眼睛望向虚空,心却早已抵达了那片灯光璀璨的赛场,去聆听球体滚过地板那坚定的回声。我看着她与安森被晚霞拉长的影子,明白运动的邀约早已超越了光明的界限,它是一道向所有坚韧心灵敞开的门。
真正将运动之魂如闪电般楔入我心底的,是在轮椅竞速的模拟训练场上。老陈,一个年近50岁的汉子,因工伤意外失去了双腿,此刻却像一头绷紧了全身肌肉的猎豹,伏在他那架流线型的红色赛车上。每一次俯身冲刺,轮椅的轮子切割空气发出尖锐的呼啸,汗水沿着他紧绷的脖颈线条滚落。那沉重的滚动声,是他重新丈量大地的脚步,是他用钢铁与意志擂响的生命战鼓。那一刻,所谓“速度”剥离了浮华的表象,袒露出最原始也最震撼的内核——是生命对禁锢的愤怒突围,是灵魂对自身无限可能的执拗求索。
在喧腾的赛场之外,运动的光辉亦如水银泻地般悄然流淌。社区小小的健身角里,我常见几位银发老者与轮椅上的邻居对弈桌上冰壶。塑料壶体碰撞的清脆声响,伴随着温和的笑语,在寻常巷陌间回荡。他们布满皱纹或行动不便的手,推动冰壶的轨迹或许不再凌厉,但那份专注与投入,分明与最高领奖台上的荣光共享着同一份热忱。运动于此卸下了胜负的甲胄,回归到最本真的面目——一种朴素而恒久的生活仪式,一种无声传递的温暖力量,让不同境遇的生命在共同的律动中彼此靠近,彼此温暖。
当运动会的圣火在夜空中升腾而起,映照的将是无数个“小舟”在黑暗中精准捕捉希望的轨迹,是无数个“老陈”以钢铁之躯碾碎命运藩篱的轰鸣。他们用身体最真实的语言讲述故事——关于跌倒与爬起,关于残缺与完整,关于沉寂与爆发。那赛场上每一次竭尽全力的跃起、每一次孤注一掷的冲刺、每一次屏息凝神的协作,都是生命在有限维度里对无限可能性的深情礼赞。
盛会终将落幕,繁华亦会归于平静。然而我深信,那些由汗水与信念浇铸的瞬间,那些在奔跑、跳跃、投掷中迸发出的生命强音,早已深深嵌入这片土地的记忆。如同博物馆里并列陈列的闪亮金牌与沉默义肢,它们无言地诉说着:运动真正的荣光与魅力,从不囿于奖牌的成色或纪录的刷新。它在于每一个平凡或不凡的生命,如何籍此击碎有形或无形的桎梏,如何在自我超越的征途上,最终聆听到内心那不屈的回响,并以此照亮各自前行的漫漫长路——这,才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关于运动的故事,一曲以血肉之躯谱写、永远向光而行的磅礴史诗。
文|张小琪 河南省漯河市文化馆 记者 柴智整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