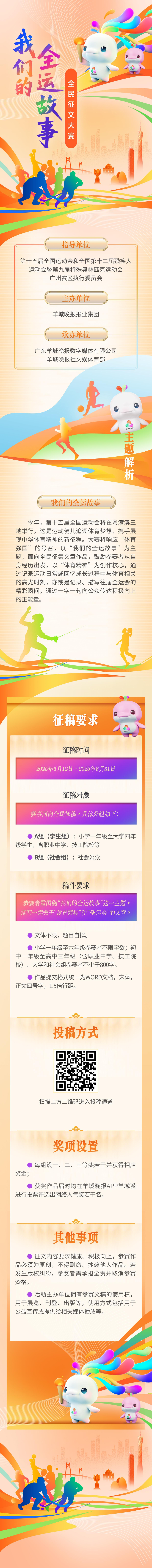我人生最初的深刻记忆,是呛进肺腑里那口冰冷刺骨的池水。
父亲黝黑的大手将我托举起来,再骤然松开。身体像一块笨重的石头,直直坠入蓝得晃眼的水底。混沌的视野里水泡翻腾上升,四周墙壁仿佛扭曲变形,水像无数冰冷的手扼住我的喉咙,我手脚拼命乱抓,却只搅动起一片徒劳的泡沫,沉重的水流无情灌入鼻腔,激得我眼泪横流。
“淹不死就行!”父亲在岸上掷地有声,像一句不容置疑的宣言。从此,每个周末清晨,那漂白粉刺鼻的气味便成了我童年固定的噩梦前调。我紧抠着池沿,冰凉滑腻的触感直抵心底,恐惧如同水草缠住脚踝,沉重得令人窒息。池水幽深如墨,仿佛随时会探出无形的手,将我拖入未知的深渊。

又一次练习换气,我笨拙地沉入水下,呛咳的酸楚灼烧着鼻腔。挣扎着浮出水面时,狼狈不堪的我几乎想要放弃。就在那狼狈不堪、泪眼朦胧的瞬间,目光无措地投向高处的窗玻璃——仿佛冥冥中的某种指引,一束跳跃的、赤金色的光芒正穿透玻璃,斜斜地倾泻下来,温柔地铺展在晃动的水波之上。
那束光,来自窗外街道上正缓缓经过的、传递着全运会圣火的队伍。人们簇拥着那团跃动的火焰,欢呼声浪隐约穿透池壁。我怔怔地凝望着那束映照在水底的光亮,它随水波摇曳、破碎又聚合,如同某种无声的召唤。恍惚间,电视里见过的运动员影像闪过脑海——他们绷紧的肌肉线条,汗珠从下颌滚落,眼神里燃烧着不灭的火焰,那是咬紧牙关也要撞向终点线的执着。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热流,突然冲开了淤积在我胸腔里的冰层。
我猛地深吸一口气,再次沉入水下。这一次,我强迫自己睁大眼睛,不再徒劳地挣扎扑腾,而是死死盯住前方池壁上那道笔直的黑色泳道标线——它如此清晰、坚定,像一条通往未知却不再令人畏惧的道路。我尝试着,笨拙地伸展手臂,努力踢动双腿,模仿着教练口中“像鱼一样”的韵律。冰冷的池水依旧包裹着我,可心里那点被圣火点燃的微光,却奇异地驱散了那浸透骨髓的寒意。
笨拙的划水与蹬腿开始了。一次次沉浮,一次次呛咳,手臂像灌了铅般酸痛,肺部灼烧得厉害。但我固执地重复着,如同中了蛊。不知何时,僵硬的四肢仿佛被某种沉睡的韵律悄然唤醒、接管。手脚的摆动渐渐有了章法,身体竟不再像秤砣般直坠,而是微微上浮,开始以一种极其缓慢但确实向前的姿态挪动。那一刻,浑浊的水流仿佛在耳畔化作奔涌的欢呼,我艰难地、却无比清晰地,一寸一寸靠近了那原本遥不可及的池壁。
当指尖终于触碰到粗糙冰凉的池壁瓷砖,我猛地从水中探出头,贪婪地呼吸着饱含消毒水气味的空气。岸上父亲的身影依旧沉默,但他紧握的拳头微微松开,眼中那常年不散的阴翳似乎被什么悄然拨动了一下,裂开一道微不可察的光亮。
此后的日子,池水不再仅是令人窒息的囚笼。我成了泳池的常客,周末清晨的固定囚徒。无数个晨光熹微或暮色四合的时刻,我独自在水中反复切割着那条幽蓝的赛道。手臂无数次酸痛到抬不起,双腿沉重如负千钧,呛水的苦涩从未真正远离。然而,每一次筋疲力竭后触壁的瞬间,每一次在极限的窒息中突破一秒的纪录,心中都清晰地回荡着一个声音:那条笔直的泳道,终于被我用笨拙却倔强的意志,一寸寸刻写进了生命的地图里。
两年后,市运会选拔赛,我站在出发台上。发令枪响,身体如离弦之箭射入水中。水流急速滑过身体,世界只剩下前方那道笔直的黑色标线。手臂划开阻力,双腿强劲打水,我奋力游向自己的彼岸。抵达终点触壁的那一刻,喧嚣的掌声骤然涌来。回头望去,泳池碧波荡漾,那条曾经让我恐惧的深蓝之路,如今在身后铺展成一条光荣的航道。
训练结束收拾泳包时,池边一个紧抓着浮板、满脸惊恐的小女孩吸引了我的目光。她死死抠着池沿,小脸煞白,像极了当年那个狼狈不堪的自己。我停下脚步,没有说任何技巧,只是朝她微微一笑,然后跃入旁边的泳道,舒展身体,用最稳定流畅的自由泳姿,在她面前游了一个来回。清澈的水流被手臂柔和地划开,身体如鱼般掠过水面。
小女孩的目光紧紧追随着我的身影,眼中最初的惶恐,如同冰雪般渐渐消融,一种细微而明亮的东西,慢慢在她清澈的瞳孔深处点燃、跃动起来。我朝岸边游去,在她面前探出头,水珠从发梢滴落。
“看,”我抹了把脸上的水,朝她伸出手,“这水里,也能走出路来。”
女孩犹豫了一下,终于怯怯地松开紧抠池壁的手指,试探着朝我伸出了小手。指尖相触的刹那,冰凉中传递着一点微弱的暖意。我轻轻托住她的手臂,如同托起一颗小心翼翼的火种。
原来体育精神真正的重量,不在于奖牌与纪录,而在于这生命与生命之间无声的传递。我父亲当年粗糙的放手,泳池深处圣火投来的微光,此刻我向小女孩伸出的手——无数双无形的手在时光里默默接力。它们将沉甸甸的勇气,从一颗心传递到另一颗心,将幽暗的深水区,点化成希望的启航之地。
这条叫做“泳道”的路,从此不再孤独。它由无数挣扎的划水、无数突破窒息的呼吸、无数牵引的手共同铺就。每个人都在其中泅渡,也终将变成后来者眼中,那束穿透深水、指引方向的微光——那小小的涟漪,终将汇入体育精神的浩瀚长河。
文|刘巧云 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子龙小学教师 记者 柴智整理